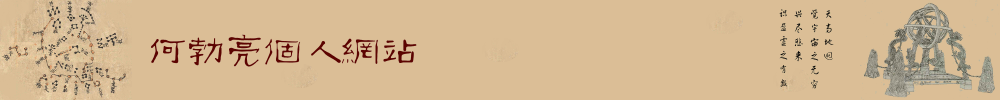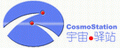●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4卷2期(1992) 转载自科学与文化网站
对于古代中国天学史的研究,即使就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至少也可认为在乾嘉诸儒考据之学中已发现其端。此后延绵不绝,直至今日。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在如此长久的传统之下、如此众多的论今之中,中国天学的起源问题(就本文标题所指的意义而言)几乎始终是被回避的。而在少数论及此事的中国学者那里,该问题的答案又几乎总是早已被预先设定——自发生成。至于如何生成和发生,则通常只有三言两语的文学性描述和推测。这一情况直到当代权威著作中仍无改变,只是改用一些较为现代的话头而已。
与中国学者的情形成为鲜明对比,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天学的起源问题却数百年来一直兴趣不衰,发表了大量专著和论文,有些在当时还引起过相当的轰动。随着时光流逝,他们的大部分工作如今已很少为人所知,他们的许多结论当然也已过时。然而他们所讨论的问题,却由此而被继承下来,构成理解古代中国天学史和上古文明史所必不可少的背景中的一部分,因而直到今天仍未失去其诱惑力和启发意义。
鉴于上述情况,本文将尝试对中国天学起源之争的有关历史略作简要的回顾与评述,并进而提出自己的一些初步看法。聊充引玉之砖,意在引起科学史界对该问题的注意——无论如何,天学在古代中国知识体系中绝不是孤立的,而起源问题对于深入理解古代中国天学史也是无法回避的。
背景: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
关于古代世界各文明的起源问题,素有两派不同的基本观点:一元论与多元论。一元论者相信上古各文明有一个共同源头,多元论者则反之,认为各种文明可以各自独立产生。
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及其后新时代的到来,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交往空前增加,致使“地球变小”。在向现代世界疾进的竞赛中,欧洲人成功地领先一步,于是他们的足迹和眼光遍及全世界,文明起源一元论也随之盛行起来。当人们在万里悬隔的不同国度历史上发现一些相同、相似事物或观念时,产生一元论思想,并进而试图探明其共同源头何在,本属自然之情理。然而这种一元论却极易招致被选为“源头”之外的民族的反感情绪——在眼前竞争中失利的人往往神经过敏。尤其是当双方都掺入民族沙文主义情绪时.学术争论很快就会误入歧途。
自逻辑角度言之,一元论者给自己招来的任务实在是过于艰巨了:既主张诸文明同出一源,则至少要阐明从源头向各方扩散传播的动力、机制和途径,而这样的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真正完成的。在此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无数难以解释的细节,并随时会面临难以完满答复的驳难。相比之下,多元论者认为各文明可独立产生,就回避了上述全部任务,自然较容易在理论上守住阵脚。加之学术日益成长,西方学者也随之从沙文主义色彩的自我优越感中解脱出来。因而上两世纪及本世纪初流行的“泛埃及说”,“泛巴比伦说”等一元论派学说,如今都已退潮。
然而,一元论的基本思想显然仍未失去其魅力。在经过一些收缩和精致化之后,一元论依旧得到不少学者——包括著名科学史专家在内——的一致支持。姑举李约瑟的论述为例:
确实,(下述观点)已经成为公认的看法,这就是:所有最古老的和最基本的发明,例如火、轮子、耕犁、纺织、动物驯养等等,只能想象为是由一个中心地区起源,而后再从那里传播出去。美索不达米亚流域最早的文明被认为是极可能的中心。……确实很难令人相信,青铜的冶炼曾经过多次的发明。但是到了晚得多的时期,如在公元后第一千纪期间,对于较复杂的发明,例如手推转磨、水轮、风车、提花机、磁罗盘和映画镜等,人们也有同样的想法。这些东西当中的任何一种,都很难想象会有两个起源。(1)
要恰当评价这段论述显然远非易事。可以指出的是,李氏在这段论述中表现出来的“泛巴比伦”倾向,与他在中国天学起源问题上所持的一此结论正相吻合.对此下文还将论及。
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西人曾提出过许多理论。这些理论通常不是假定华夏区域的土著接受某种西方文明,而是作釜底抽薪之论——论证中华民族系从西方迁来。最早出现者为埃及说,发端于耶稣会士柯切尔(A.Kircher)。柯氏曾发表《埃及之谜》(罗马,1654)和《中国礼俗记》(阿姆斯特丹,1667)两书,从中文与埃及象形文字相似之处出发,论证中国人为埃及人之后裔。稍后有1716年法国主教尤埃(Huet)著《古代商业与航海史》,主张古埃及与印度早有交通,故埃及文明乃经印度而传入中国,进而认为中、印皆为古埃及人之殖民地,两国民族则大多为埃及血统。著名法国汉学家德经(J.de.Guignes)也力倡中国为埃及殖民地之说,他可说是持中国文明源于埃及之说者中最著名的人物。德经于1758年11月14日发表题为《中国人为埃及殖民说》之演讲,从汉字与古埃及象形文之相似立论,进而称中国古史实即埃及史,甚至考证出埃及人迁居中土之具体年代(1122 B.C.)。(2)此外持类似观点的尚有S.de.Mairan(1759)、Warburton(1744)、Needham(1761)等人,立论之法各有异同。同时反对者也有不少。而至本世纪,这些学说都已失去其影响力。
当埃及说逐渐衰落时,又有巴比伦说代之而兴,主张中华民族源于巴比伦。19世纪末,伦敦大学教授拉克佩里(T.de Lacouperie,法国人)发表《中国上古文明西源论》一书,认为中华民族系由巴比伦之巴克族东迁而来,且将中国上古帝王与巴比伦历史上之贵族名王一一对应,如谓黄帝即巴克族之酋长、神农则为萨尔贡王(Sargon)等等,并找出双方在文化上大量相似之处。(3)拉氏之说出后,一时响应者颇多。至1899年有日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著《支那文明史》,进一步发挥拉氏之说,且列举巴比伦与古代中国在学术、文字、政治、宗教、神话等方面相似者达七十条之多,以证成其说。1913年英国教士鲍尔(C.J.Ball)作《中国人与苏美尔人》一书,也持同样之说。
与埃及说问世之后的情况不同,巴比伦来源说问世后竟一度大受中国学者欢迎,本世纪初响应之作纷起,如丁谦《中国人种从来考》、蒋智由《中国人种考》、章炳麟《种姓编》、刘师培《国土原始论》、《华夏篇》、《思故国篇》、黄节《立国篇》、《种原篇》等,皆赞成或推扬拉氏之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在今天看来非常令人惊奇的现象,方豪的解释是,“此说最受清末民初中国学人之欢迎,以当时反满之情绪甚高,汉族西来之说,可为汉族不同于满族之佐证。”(4)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共和国一流学术权威的著述中,巴比伦来源仍未受到断然拒斥。例如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一书,初版于1931年,共和国成立之后又曾三次重印(人民出版社,1952;科学出版社,1961、1982),在其中仍可见到如下论述:
似此,则商民族之来源实可成为问题。意者其商民族本自西北远来,来时即挟有由巴比伦所传授之星历智识,入中土后而沿用之耶?(5)
由此可见巴比伦来源说确有相当的生命力。当然,此说同样有许多反对者。
以上西源之说,今日虽已不再流行,但因古埃及象形文字与汉字确有许多惊人相似之处,巴比伦与古代中国在天学方面的相似之处也不易完全否认,有此类理由为支柱,西源说自问世后,终能不绝如缕,不仅常被后人提到,而且还能唤起勇敢者旧论重提的雄心(下面将会谈到一个这样的例子)。此外,在华夏民族西源说的大方向下,还有诸如印度说(A.de Gobineau)、中亚说(R.Pumpelly等)、新疆说(Richthofen)、蒙古说(R.C.Andrew等)等不同主张。国人卫聚贤也曾从容貌(发、须、目、鼻)、语言文字、风俗、货币、帝王世次记法、文法等七方面,在中国古籍中搜讨证据,主张夏民族为亚利安人种。(6)又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on)从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之彩陶与西方考古发掘所见彩陶之相似立论,主张中土彩陶文化系发源于西方而后东传。(7)其说也保持着相当持久的影响力。
文明起源一元论并不仅仅导致泛埃及、泛巴比伦之类的西源说,它同样还可导致相反的极端——不妨名之曰“泛中国说”。比如1669年有J Webb创中国语言为古代人类公用语之说,1789年又有D.Webb主张希腊语源出中国,等等。这类想当然极易受到国人的青睐,在此方向上不乏继起之作。其中较重要者可以提到顾实。顾实致力于中国历史上一部争议很大、充满谜案的奇书《穆天子传》的研究,他坚信该书中所记载的周穆王远行实有其事,所行之处则远至欧洲大陆,最后的结论更是充满狂想激情:
则周天于疆宇之广远,岂非元蒙古大帝国之版图尚或不能等量齐观,而不可称人类自有建国以来,最大帝国、最大版图,当推周穆王时代哉!……则即发现上古我民族在人文上之尊严,与地理上之广远,均极乎隆古人类国家之所未有,可不谓曰我民族无上光荣之历史哉!(8)
其说之不足信据是显而易见的。约略与顾实同时,又有姚大荣的论著,更堪称“泛中国说”之标本。姚氏著《世界文化史源》一书,卷帙浩繁,未曾刊印,仅有他私家印刷的该书提要行世。姚氏也从《穆天子传》入手,但又发挥邹衍“大九州”之说,最终竟断言上古世界诸文明的总源在华夏,而华夏古帝皇曾是全球最高统治者,至于埃及、巴比伦则不过后来独立之诸侯云云,充满奇情异想。这类学说到今日大体上仅剩下史料价值。
令人迷惑的中国天学西源说
在古代文明起源及传播问题中,天学实占有一种特殊的重要地位,原因至少有三:(1)天学作为一门高度复杂抽象的学问,足以成为衡量一民族开化与文明程度的理想标尺之一;(2)天学是一门精密科学,许多天象皆可用现代方法准确逆推,在解决古史研究中年代学之类的问题时,常能独擅胜场;(3)天学在古代东方型专制政治中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9)因此在各种中国文明西源说中,经常将论证中国天学源于西方作为其说的重要支柱。事实上,西方学者数百年来对中国天学起源的探讨,是与探讨文明起源这一背景完全分不开的。
论证中国天学源于西方,这在文明起源一元论中固是题中应有之义(“泛中国说”自然例外),但对多元论来说也同样可以采纳。因为即使承认中国文明独立发生,仍可认为其中的天学知识系从西方输入。
论证中国天学西源的尝试,在早期中国文明西源说中已见端倪,稍后即有专著问世。法国人巴伊(S.Bailly)于1775年发表《古代天文学史》,其中研究了巴比伦、印度与中国的古代天学,断定三者同出一源——源于一个可能曾位于亚洲大陆北纬49°附近某处而现已消亡的民族。(10)其说颇为玄虚.作为立论基础,他对三大古代天学的理解也难免失之浮浅。但仍不失为从天学本身论证中国天学西源说的一次认真尝试。此后这种中国天学西源说的观点在法国汉学家中颇有传统。比如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著名汉学家马伯乐(H.Maspero)仍主张类似学说。马氏认为古代中国天学中大部分成分是受到西方启发后才出现的:在大流士(Darius I,521--486 B.C.在位)时代从波斯和印度传入二十八宿、岁星纪年、圭表和漏壶;稍后在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334—325 B.C.在位)时代传入十二循环法和星表体系,等等。(11)但后夹马氏自己也不再强烈坚持这些很难站得住脚的结论。
在中国天学西源说发展史上,日人饭岛忠夫与新城新藏之间的激烈论战特别引人注目,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也较此前各说为大。饭岛自1911年起发表一系列文章,力倡中国古代天学体系来自西方之说,新城则持相反意见。两人交替发表文章和演讲,相互驳难。饭岛1925年出版《支那古代史论》(12),全面阐述其说。他认为中国天学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建立体系,该体系是从西方输入的,直接的理由有十条:
1、中国古代的宇宙生成论与古希腊人的相似。
2、中国四分历取回归年长度为 日,古希腊Eudoxus也取同样数值
3、由四分历回归年长度和19年7闰法则,可得76年周期(即从历元时刻起经76年之后,合朔与冬至时刻又回到同一天同一时刻),而古希腊Clippus也在330B.C.左右创立同样的周期法。又中国与希腊都曾以428B.C.这年的冬至日午前零时为历元。
4、古希腊制定76年周期法所依据的观测完成于400B.C.左右,而巴比伦之测定春分点与古代中国之测定冬至点也恰在同一时代。
5、楔形文泥版书中所见巴比伦星占学,其中有些内容与《史记•天官书》相似;而巴比伦星占学在公元前四世纪左右传入希腊。
6、中国二十八宿体系与巴比伦和印度的同类体系同出一源。
7、巴比伦与印度皆有与中国相似的木星(岁星)纪年法,而印度此法又系西方输入。
8、《春秋》所记36次日食中,有两次为中国全境所不能见,但用巴比伦推算日食之沙罗周期(Saros)推算之则正相吻合。
9、中国古代天学仪器如圭表、漏壶、浑仪等,与古代西方颇相似。
10、古代中国乐(律)历相关,此与古希腊Pythagoras学说相似。
至于古希腊天文学东来的途径和方式,饭岛仅有猜测之辞,他将中国战国时代的学术繁荣与亚历山大东征联系起来。
饭岛依靠上述证据支撑的中国天学西源说,确实很难成立。上述十条证据中,有的本身尚待证明(比如6),当然难以持为证据,大部分则都暗含了“相似即同源”的先验判断(这又要引导到前述一元论与多元论的原则问题上去)。而饭岛的论敌新城则在并不否认“相似即同源”的情况下,力辩中西天学并无饭岛所说的那些相似之处,他的结论是:
要之,自太古以来至汉之太初间约二千年,中国之天文学史全系独立发达之历史,其间丝毫未尝有自外传入之形迹。(13)
然而饭岛之说却受到一些中国学者的欣赏,之所以会如此,另有一层背景。
饭岛之意,本不止于论证中国天学之西源,而是要从天学入手,全面重新考察“支那古史”。主要做法是试图从天学内容去考证一些重要古籍的年代。他的结论竟是断定《诗经》、《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等书“皆为西纪前三百年附近以后之著作”。而对于由大量考古发现如商周青铜器、殷墟甲骨文等揭示的无可怀疑的中国上古文明史,饭岛竟倾向于抹杀或否认(他甚至怀疑青铜器和甲骨文是后世伪造)。但是饭岛之说问世时,恰值中国学术界疑古之风大炽,许多古籍都被指为后世伪造或假托.或被指为曾经过刘歆等人的篡改。于是饭岛之说适逢其会,被引为疑古派的同盟和友军,刘朝阳的论述可作为当时这种想法的典型例证:
案饭岛之说,虽不能必其全能成立,然其所谓现存中国古籍皆在西纪前三百年附近以后出世之结论,极为可靠。在国内前次所引起之古史论战场上,此结论或可为顾颉刚之一有力帮助。(14)
当然,随着时代变迁与学术演进,《古史辩》派所代表的学术思潮早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而矫枉过正,将结论推得过远,最终也不免重新退回来。饭岛之说虽在天学史研究上仍有一些参考价值,总的来说则早已归于沉寂。
关于古代中国天学可能来源于西方的猜测和探索,在当代仍保持着活力,受到一些著名学者的支持。这里姑举郭沫若、李约瑟两人为例。郭、李两人名满天下,皆为中国学者所熟悉,然而他们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在国内却极少受到注意,其中原委,可能颇为微妙。
郭氏关于殷民族可能来自西方、来时可能已携有巴比伦天学知识的推测前已引述,他在别处也谈过这样的观点,兹再引述一二:
这个新的问题根据作者的研究也算是解决了的,详细论证请看拙著《甲骨文字研究》的《释支干》篇,在这儿只能道其大略:便是十二辰本来是黄道周天的十二宫,是由古代巴比伦传来的。(15)
就近年安得生对彩色陶器的推断以及卜辞中的十二辰的起源上看来,巴比伦和中国在古代的确是有过交通的痕迹,则帝的观念来自巴比伦是很有可能的。((15) 330页)
需要指出,郭沫若并非“全盘”的中国天学西源论者,他只是主张中国天学中有重要基本成分系来自西方。例如他对二十八宿就主张中国起源说(5)。但他的《释支干》确是一篇非常渊博而又极富启发性的力作,文中关于巴比伦黄道十二宫等天学知识于上古传人中土之说也颇能言之成理。国内在这方面迄今尚未出现堪与之比肩的后起之作。
与郭沫若相仿,李约瑟也并非“全盘”中国天学西源论者,但他所论西源部分的重点,却恰与郭沫若构成“互补”情形——他一再强调二十八宿源于巴比伦。李约瑟在这方面的论述极少受中国学者的注意,却曾受到某些堪称巧妙(!) 的歪曲(16),因此有必要稍多引述一点,以明真相。李约瑟在提到伏尔泰(Voltaire)与巴伊之间的争论时说:
前者为印度和中国的成就辩护,后者则极力贬低。不过,巴伊在他的议论中有一点是猜想得对的:他说印度和中国的科学至少有一部分来自它们更古老的文明。(17)
巴伊的学说已见前述。李约瑟此处所说比印度与中国“更古老的文明”,据其著作中多次论述可知所指正是巴比伦。例如:
中国、印度和阿拉伯等三种主要“月站”体系同出一源,这一点是几乎无可置疑的,不过来源何在却是极为古老的问题。......奥尔登贝格(Oldenberg)在一篇重要论文中提出一种说法,他认为巴比伦有一种原始型“白道”(lunar zodiac)为亚洲各民族所普遍接受,这三种体系都是从这种白道发展起来的。((17),186---190页)
我本人一直相信绕赤道的月站原始圈是起源于巴比伦的,以致根据这样的情况,我将高兴地同意阿博博士(Dr.Aaboe)在这个会议上所讲的巴比伦起源的重要性,惟一的困难是不能从巴比伦天文学中推衍出二十八宿和“纳沙特拉”来。(18)
进一步的研究将会发现,这一体系(指二十八宿——引者按)或许更可能是巴比伦的创造,然后向几个方向传播,到达印度和中国。(19)
所谓“二十八宿”,即位于赤道或其近处的星座所构成的环带,是中国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的天文学所共有的。一些对这几种文化的古籍原文很少了解或毫不了解的著作家们,采取各执己见的态度,经常作出武断的论述。我们以后将指出,二十八宿的发源地可能不是这几个地方当中的任何一个,它们关于二十八宿的概念统统是从巴比伦传去而衍生的。((17),7--8页)
从上面这些论述看,李约瑟的“泛巴比伦主义”倾向是相当明显的。他的这些观点,与他那些热烈讴歌中国古代成就的论述相比,可以说在中国学术界是大受冷遇。
文明起源旧话重提
前已指出,中国天学的起源问题是与中国文明起源这一大背景无法分开的;因此,当后者在近年再次被郑重提起时,我们理应予以足够的重视,而且,有些新尝试已明显超越了前代西方汉学家处理同一课题的学术水准。其中苏联学者列•谢•瓦西里耶夫的新著尤为引入注目。
瓦氏新著书名就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全书以“阵地战”方式,对所论主题全面清算,进而提出新的假说。瓦氏抛弃了以往文明起源一元论的陈旧简单模式,而代之以一种“梯级一传播”的理论,其要旨如下:
如果说文化相互作用和扩散的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比作连通的血管系统,那么这种相互作用的实际结果、成就和处在人类及其文化进化过程中不同水平的人类居住地区的传播便可以想像为一种有许多梯级的金字塔。(20)
按瓦氏之说,上古文明可以多元发生。开始各地人群都竟相攀爬文明进化之金字塔,在早期阶段仍适用“传播决定论”,即对外接触与外来影响这一竞赛起主要作用。而一旦上到文明的门槛——瓦氏所设想的金字塔第四台阶,则外部影响变成次要。故文明产生的过程有如下特征:
突破完成得越晚,即最初文明的某个发源地发生得越晚(而中国文明的最初发源地在旧大陆是最后一个),其他文明的文化成就能起的作用就越大。((20),38页)
在上述理论框架之下,瓦氏构造出他自己对于中国文明起塬的假说,认为中国文明是土著文化(早殷青铜文化)与一西来之较高文化融合的产物。该西来文化由一支“目前尚不知道的”草原部落带来,而该部落当时“已有了象形文字体系和天文历法,掌握了艺术的技巧”。也就是说,在瓦氏的新假说中.中国天学也是源于西方的。其说与郭沫若早年的猜测颇有相合之处。
显而易见,“梯级—传播”理论较之一元论或多元论,融合说较之先前的西源说或本土说都要精致得多。其包容量更大,能解释的现象和疑问更多,因而在理论上也更经得起驳难。在这种理论框架中的中国天学西源说.是一种“上古传入说”。下面就将看到,这比饭岛或马伯乐之类的“晚近传入说”要容易自圆其说。
从文化功能看中国天学起源
本文作者曾探讨了古代中国天学与王权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此阐明古代中国天学的文化功能。((9)详细而系统的分析论证则见(16)第三章)同时,古代中国天学极强的继承性和传统也是众所周知的。这样,就有可能为讨论中国天学起源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在相当大一部分中国天学西源论者心目中,天学在中国上古文化中的地位及功能或许与在古希腊文化中并无不同——主要是他们对于古代中国文化缺乏深入理解之故。许多学者想当然地将古代中国天学视为与现代天文学同一性质的事物。因此他们先验地认为,古代中国的天学可以像其他某些技艺那样从别处输入,就好比赵武灵王之引入胡服骑射,或者汉武帝之寻求大宛汗血马那样。换言之.他们认为古代中国可以在自身文明相当发达之后,再从西方传人天学。但是,只要明了古代中国天学与王权的相互关系,所有这类主张“晚近传入”的西源说都将不攻自破——原因很简单,古代中国天学的文化功能决定了它只能与华夏文明同时诞生,它在华夏文明建立过程中既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就不可能等到后来才被输入进来。
然而,对于另一类中国天学西源说,即主张中国天学早在上古时期就己从西方传人——这类学说通常都要和中国文明西源说的大理论结合在一起,则看来阐明中国天学的文化功能尚不足以构成否定它们的理由,因为按照这类学说,华夏文明本身就可能是由某一支西来文化发展而成,而天学是该文化东迁时已有的(如前述郭沫若的猜测);或者华夏文明是某个西来文化与土著文化融合而成,而天学是由西来者带来的(如前述瓦西里耶夫之说),总之天学的西来是在华夏文明确立之前或同时。这样就与中国上古天学的文化功能并无矛盾。
至此,或可得出如下较为保守的结论:
古代中国天学起源甚早,它在较晚时期(例如战国时期)才从西方传入的可能性可以排除。中国天学的起源问题是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分不开的,而此两问题都还有进一步研讨的余地。
在此还有两点需要略加申论:
一是研究起源问题的意义。像中国天学的起源这类问题,几乎可以断言是不可能得出确切答案的。已出的中外各说都很难成为定论。事实上,这类课题不妨视为纯粹“学术操练”的场地或项目——也许永无定论,但不断会有人来作新的尝试。只要抛弃夜郎自大、沙文主义、神经过敏、辉格倾向等等的非学术情绪,心平气和,则人人皆可登场,互较各自假说的优劣。虽然难有定论,但研讨起源问题有着非常积极的启发作用,例如,迄今为止围绕中国天学起源问题的种种争论,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古代天学就能产生很大的促进。学术的进步,本来就更多地体现在研究探讨的动态过程之中,而不在于一言既出众口息喙的“定论“的积累之下。
二是对古代中国天学体系的认识。尽管关于中国天学究竟源于西方还是自发生长的问题中外学者众说纷纭,但对于中国天学有其自身体系这一点基本上无多异议。因此可以说,即便中国天学真是上古时自西方传来,那它也早已在华夏文明建立的过程中受到吾土吾民(不管从人种学上说他们来自何方)创造力的滋润和养育,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面貌。而且,该体系在此后漫长岁月里一直牢固保持着。六朝隋唐时代,各种西亚、中亚和印度的天学虽曾在中土广泛传播,((16),第六章)但当它们形成的浪潮退去之后,中国传统天学在整体上竟几乎毫无改变,至多只是采纳了某些技术性成就以充实自己的体系而已。这和古代印度天学随着不同异域文化的进入而屡次改变自身结构面貌(21),恰成意味深长的对比。
参考文献:
(1)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240—241页,科学出版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J.de Guines; Memoire dnas lequel on prouve, que les Chinois sonl une Colonie Egyptienne, Desaint & Saillant, Paris(1760)
(3)、T. de Lacouperie:The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London(1840)
(4)、方豪:《中西文通史》,32页,岳麓书社,1987。
(5)、郭沫若:《释支干》,《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284页,科学出版社,1982。
(6)、卫聚贤:《古史研究》第三集,36—4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7)、J. G.. Anderson: An Early Chinese Culture,《地质汇报》第五卷第一期(1921)。
(8)、顾实:《穆天于传西征讲疏》,《读穆传十论》,31页,自序2页,中国书店,1990
(9)、江晓原:《天文•巫咸•灵台——天文星占与古代中国的政治观念》,《自然辩证法通讯》13卷3期(1991),系统的论证可见(16),第三章。
(10)、S. Bailly: Histoire del’ Astronomie Ancienne, Paris(1775).
(11)、H. Maspero:La China Antique, Paris(1927).
(12)、饭岛忠夫:《支那古代史论》,东洋文库,1925。
(13)、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沈璿译,22页,中华学艺杜,1933。
(14)、刘朝阳:《饭岛忠夫< 支那古代史论>评述》,《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No.94—96(1929),68页。
(15)、郭沫若:《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327—328页,人民出版社,1982。
(16)、江晓原:《天学真原》。308—309页,辽宁教青出版社,1991。
(17)、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中译本题为第四卷),14页,科学出版社,1975。
(18)、李约瑟:《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天文学》,《李约瑟文集》,479—480页,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
(19)、李约瑟:《古典中国的天文学》,同(18),466页。
(20)、列•谢•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郝镇华等译,34—34页,文物出版社,1989。
(21)、D. Pingree : History of Mathematical Astronomy in India,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New York(1981), Vol. 16, P. 534.